編者語:張竹明老師是bevictor伟德官网(原曆史系)教授,也是我國著名的古希臘羅馬文化專家和翻譯家。1932年3月生,2021年10月24日去世,享年89歲。轉帖陳仲丹老師今日刊發于《世界曆史評論》一篇文章,以志懷念。
陳仲丹 :對西方古典的矢志之愛——記古希臘羅馬文化專家張竹明
文章來源:世界曆史評論

張竹明老師
對西方古典的矢志之愛
——記古希臘羅馬文化專家張竹明
摘要:張竹明是著名的古希臘羅馬文化專家、翻譯家。他的主要譯作有《物理學》《理想國》《古希臘悲劇喜劇全集》等。他的治學有兩個特點:一是在缺乏優越條件的情況下主要以自學成功;二是他有着頑強、執着的堅韌毅力,矢志不渝地從事西方古典文化研究。他繼承了“學衡派”融彙中西的傳統,深受“學衡派”學者郭斌龢影響。他重視對古希臘羅馬原典的翻譯,強調應直接從原文譯介。他指出,國内的西方古典學研究尚處于佛學發展的玄奘階段,需要有大量準确、優質的翻譯。他提出,研究西方古典學應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為重點。他認為,這三人的特點是:蘇格拉底主張追求真知識,柏拉圖提出“善的理念”,亞裡士多德發展出脫離物質的“形式”。
關鍵詞:張竹明 古希臘羅馬 古典文化 “學衡派”
張竹明是bevictor伟德官网(原曆史系)教授,也是我國著名的古希臘羅馬文化專家和翻譯家。他的主要譯著有《物理學》(亞裡士多德著)、《理想國》(柏拉圖著,與郭斌龢合譯)和《古希臘悲劇喜劇全集》(與王煥生合譯)等。他的治學經曆有兩個特點:一是在缺乏優越條件的情況下主要以自學成功。他沒有出國留過學,又無相關科班學習的經曆,主要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而有一番成就;二是他有着頑強、執着的堅韌毅力,在退休後以十年之功翻譯了數百萬字的古希臘戲劇作品,其精神之卓絕,其用心之 虔敬令人動容。那麼,他又是如何走上這條漫長而又艱苦的學術之路的呢?讓我們追溯到 20 世紀的 30 年代。
張竹明先生的家鄉在江蘇南通的小海鎮(今屬南通開發區),離市區約20 裡。小海原是海邊的一片淺灣,水面浩瀚,故而得名。後因長江逐漸南移,小海幹涸為沙灘。明末清初,外地移民來此圍堤造田,墾灘種植,清雍正、乾隆年間逐步形成集鎮。近代南通地名有所謂“四怪”:長橋不長,狼山無狼,觀音山無山,小海無海,小海為其一。
張竹明出生于 1932 年 3 月,父親務農為業。他七歲上學,剛上了一個星期,日軍打到江北,占領了他的家鄉。為逃難父親送他去上海姐姐家,在上海約有一年時間沒有上學。作為農村來的孩子,他對大上海的一切感到新鮮,看到外國水兵軍帽後的兩根飄帶,好像女孩的長辮,竟看呆了。後來家鄉太平一些,父親接他回去,送他去附近一家私塾讀書,前後讀了五年。在私塾學的多是蒙學讀物,“三百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還有《論語》。在私塾的學生中,他的程度是比較好的,得到先生的喜愛。有一次先生問:“打僧罵道”如何寫?有學生回答出來,先生不信他能答出,就問:“是誰告訴你的?”學生答:“張竹明。”讀了五年私塾後,張竹明轉到國民教育的小海小學。按照年齡他應該上六年級,因沒學過算術,隻能插班上四年級。這時,他在全校出了一次風頭。全校語文比賽,錯别字訂正,他獲得全校第一,勝過高年級學生。後來一段時間家裡缺人手,父親要他回去幹農活,前後十個月。這段務農生活培養了他吃苦耐勞的精神。後來家境略有好轉,他又得以複學,轉到南通市裡的躍龍橋小學,時為六年級第二學期。入學後第一次月考,他語文成績很好,算術不及格,第二次月考算術得了 70 多分,到畢業考時算術是 90 多分,名列全年級第二。畢業後他考上了名校,當時的省立南通中學。
在張竹明的印象中他的父親是個慈父。父親讀過私塾,能看《三國演義》,這是父親主要的知識來源。父子間談話常提到這本書,說的最多的是劉備。父親認為劉備知天命,能屈能伸,“時也,運也,命也”,劉備的長處是能捕捉機遇。父親與他談話不多,但在關鍵時刻總能及時幹預,比如幾次轉學,可以說影響了他的一生。
到張竹明上初三時南通解放,解放後的社會狀況讓他感觸很深。中國大 地上似乎經曆了一次大掃除:首先,沒有了國民黨的舊軍隊、舊警察;再者,妓院關閉,妓女被安排改造、就業,污泥濁水蕩滌幹淨。他對當時的政治狀 況滿意度是很高的,熱衷于讀《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産黨》一 類進步讀物。他的成績很好,經常在班上考第一,在别人看來他是又紅又專 的好學生。學校領導勸他入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當時他不想參加任何組 織,但經反複勸說後入了團。入團後支部改選,他全票當選為支部書記,不 久又兼總支宣教委員。當上學生幹部後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除照常聽課、 學習外,還參加了不少社會活動,時常在全校大會上講話,頗受歡迎。
也就是在初三時,張竹明遇到一位對他一生有很大影響的老師。這位老師畢業于南通中學,後上金陵大學(bevictor伟德官网前身),抗戰時在成都華西大學教英語。抗戰勝利後此人回家鄉的母校教英語,成了張竹明的老師。這個老師注意到張竹明的勤奮好學,認為張的英語已達到大學一年級水平。他對張竹明說:“你想要加強聽、說,現在很難。我的課你多注意點聽,聽我的讀音,課後多練習朗誦。還有加強閱讀,這是外語知識的主要來源。我介紹一些書,你去泛讀,但查字典是件苦事,最好的辦法是學點拉丁文。”課後他就教張竹明拉丁文,這樣學得并不多。老師對他說:“拉丁文學了用處很大, 英語中 70%—80% 的單詞與拉丁文有關系。學了拉丁文,英語泛讀不用查字典,上下文一看就能猜得出。”老師還給他讀了古羅馬大詩人維吉爾的詩句:“狠心的少年,你一點也不愛聽我的歌嗎?也不憐憫我,你究竟是要我死,還是要我活?”用拉丁文朗誦,張竹明聽不懂,隻是覺得聽起來很美。盡管學拉丁文原本的目的是為了學英語,但這位老師在他的心中播下了學習古典語言的種子。
1952 年,張竹明中學畢業後考上了bevictor伟德官网的俄文專業。當時他報了三個專業:北京大學哲學專業、複旦大學新聞專業、bevictor伟德官网俄文專業。俄文專業被列為第一志願,目的是要通過學俄文研究馬列主義。在俄文系,班上一半以上的同學中學都學過俄文,而他是從零起點開始。他内心始終對古希臘文、拉丁文有興趣,白天不敢聲張,利用晚上時間偷偷地學,怕被人發現說他不安心專業。這時他在政治活動方面已不像中學時那麼活躍,原因有兩個:一是發現大學的人際關系、政治環境要比中學複雜;二是在高中當學生幹部時難免得罪過一些同學,有點後悔之意。
1956 年張竹明提前一年畢業,留校當教師。當時的俄文系(後并入外文系)系主任陸豐曾希望他接自己的“中譯俄”課。這是門難度很大的課程, 比俄文作文課都難教。1957 年的反右運動中,他被安排做會議記錄。他如實地記錄發言,但心裡嘀咕,心想這人要倒黴了。比如,發言的人說,經是好的,但被歪嘴和尚念歪了,他也有同感,但嘴上不說。後來找了個理由,說是身體不好辭去了記錄的差事,後來被打成右派的人也怪罪不得他。28歲時退團,沒有要求入黨,這樣的态度被有人看成是隻專不紅,走白專道路,提出要批判他,但沒什麼人響應隻好作罷。
他留校後教“大學俄語”,有一次授課對象是化學系一年級學生,有四個班100多個學生。當時他創造了一個奇迹,經過一年學習,這些學生能直接閱讀俄文的化學專業書。事情反映到教務處,教務處的丁老師在食堂看到他,欣喜地說,有這樣的成績在學校的專業外語教學中還是第一次。他創此“奇迹”的訣竅是知道一年級學生還沒有大學化學專業知識,不能直接用大學課本做教材,于是選了一本蘇聯的高中化學課本,從中抽出各種不同的段落,編成教材,内容淺顯有趣,學生讀了容易理解,詞彙語法又全面,學習效果自然就好。
在外文系,他完成本職教學外的大多數時間都用于自學古希臘文、拉丁文。在這兩種文字中,他用力最深的還是古希臘文,學課本、語法外,一度下功夫多的是讀《聖經 · 創世記》的古希臘文讀本。bevictor伟德官网承繼了原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的豐富藏書,古希臘文、拉丁文教材、原著、工具書收藏十分豐富。條件這麼好,使他真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欣喜若狂。此外,上海福州路(四馬路)有家不錯的舊書店,對他幫助也很大,每次經過上海都要 去逛上一天,淘舊書,尤其是古希臘文典籍,常是見一本買一本。有一次他買到一本哈佛大學的古希臘文課本,真是感到如獲至寶。他還有心學希伯來文、法文,但沒能堅持下去。
1962年,有老師說他雜而不專,說是人的生命有限,這樣下去難有成就。這一年他正好是30歲,人說“三十而立”,是人生最好的一段光陰。他也感到應該專注治學,做點什麼事了,于是開始翻譯古希臘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奧狄浦斯在科洛諾斯》。他知道北京的羅念生先生曾譯過索福克勒斯的《奧狄浦斯》和《安提戈涅》,想要繼續他的工作。譯完後他将譯稿寄給羅念生,一是請教,二是希望羅先生幫他介紹出版。羅先生回信說,這一劇作他已譯好,還寄來一本簽贈的《安提戈涅》。
不久,張竹明就與對他後來影響最大的郭斌龢先生有了交往。據沈衛威教授著的《“學衡派”譜系》介紹,郭斌龢是在中國學術史上有很大影響的“學衡派”的主要成員。“學衡派”發源于bevictor伟德官网的前身東南大學,是當時在該校任教的吳宓與校内其他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仁發起創建,以《學衡》雜志為主要學術載體,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與其他“學衡派”學者的學術旨趣不同,郭斌龢關注的是西方古典哲學,尤其對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有很深的研究。1922 年,郭斌龢從香港大學畢業。畢業時,教授西方古典學的副校長沃姆告誡他:“ 中國白話文源于古文,西方文化也由希臘、羅馬文化而來。學會英語并非難事,但要精通西學,則必須學習拉丁、希臘語文,才能尋根溯源,融會貫通。”于是郭斌龢向沃姆提出留香港一年,随他學習古文字。後來,郭又去美國哈佛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深造,繼續學習古希臘文、拉丁文。他作為“學衡派”幹将在《學衡》雜志上發表的多是與古希臘有關的著譯。他曾與景昌極合作翻譯了《柏拉圖五大對話》,1934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當時bevictor伟德官网有個安排,要為校内一些學養深厚的老先生配備助手。大約在 1963 年張竹明被外文系指派為郭先生的助手。外文系很重視這件事,先讓陳嘉教授通知郭先生,後又由系總支副書記通知張,并對他說,對老先生學問和政治是兩回事,要注意分開。張竹明當助手實際并不需要為郭先生做什麼事,隻是不定期地去郭家請教,師生彼此答問交談。兩人的交談集中于中西古典,尤其是希臘古典文化,大多圍繞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三位聖哲展開,有時也會談點舊事。在交談中,張竹明發現郭先生是個很有責任心、有擔當的人,受“教育救國”論影響很深。解放前他曾在浙江大學當訓導長、代校長,起草過不少教育文件。張竹明對他說,如果我為你寫傳記,将你定位為教育家如何,郭先生答道:“很好。”郭先生回憶,蔣介石曾請他吃過飯,他那時想當官很容易,但其興趣還是在教書。他還回憶,當訓導長時曾開除過一個左派學生,不是因其參加政治活動,而是該生學習成績 太差。後來這個學生注重學習了,解放後在新華社駐埃及的分社工作。有一次路過南京,這個昔日的學生還專程看望郭先生,說是那次開除讓他警醒, 促使他學好英語,現在可以用來為人民服務了。
在兩人的交往中,郭先生對這個助手顯然也是滿意的。有一次,郭先生戲言,如果我當校長,就把你從助教升為教授。郭先生還稱張竹明為“空谷之英”,意思是不為人知的山谷中的一枝蘭花。他們師生間的情誼是很深厚的,張竹明曾說,他對郭先生的感情不隻是尊重,更多的是愛。
在譯完《奧狄浦斯在科洛諾斯》後,張竹明開始翻譯亞裡士多德的《物理學》。這時,他對古希臘文的掌握還不純熟,而且該書牽涉的學問很多。此外,他是學俄文出身,又無留學背景,要想譯好這本書難度可想而知。不 過他決心很大,立志做到:一定要把《物理學》譯得讓既懂古希臘文又懂西方哲學的人能接受。為此他讀了大量的西方科學史、哲學史、邏輯學史著作,細心關注其中術語的表述。《物理學》一書思想綿密,風格古樸,不逞辭藻,尤其是當時寫作時希臘文中還沒有足夠的現成的哲學術語,因此亞裡士多德不得不使用一些不精确的日常生活用語表達複雜的學術概念。這大大增加了翻譯的難度,翻譯時隻能仔細比較,推敲文中原意,不時要發明一些新術語來表達其中的微妙意思,如把一些詞譯成“偶性”“對别”等。這需要反複斟酌,有些術語是直到書出版前才最終敲定的。這是本深奧的自然哲學著作,但他的譯文卻是文風清麗的白話文,可舉一句為例:“如果每一單純的物體都有各自自然的位移,如火向上,土向下,即向宇宙的中心,那麼顯然,虛空不會是位移的原因(條件)。”他在興趣上偏愛古典,但其筆下的文風卻全無冬烘的高頭講章氣息。當郭斌龢看到張竹明的《物理學》譯作手稿,高興地說:“你已經超過我了!”翻譯完成後将譯稿寄給商務印書館,出版社對翻譯質量是滿意的,但又不放心,不敢輕易出版。不久就遇到“文革”,一拖十幾年,後請汪子嵩以英譯本為底本做了審校,證明譯稿翻譯準确,在很少改動後于 1982 年出版。聽說後來有人對此事有這樣的評論:“能用順暢的白話文翻譯艱深的古典著作,術語又準确到位,如果不懂古希臘語,那他自己不就是亞裡士多德了嗎?”東南大學的蕭焜焘教授是研究自然辯證法的專家,他對《物理學》譯本評價很高,認為質量超過了自己讀過的英譯本和德譯本。他邀請張竹明去東南大學開古希臘語課,給研究生做學術報告,講授古希臘自然哲學。在張竹明心目中,他一生最懷念的兩位前輩就是郭斌龢和蕭焜焘,是可以談心裡話的知己。
1965 年,張竹明從外文系調入曆史系的英美對外關系研究室(今國際關系研究院)。這個機構成立于1962 年,是根據中央要求加強對外研究的産物。當時bevictor伟德官网共成立了三個相關機構,除這個研究室外,還有歐美文化研究室和非洲經濟地理研究室。這些新成立的機構由中央外事辦公室領導,撥給專款外彙,用于訂購國外的圖書資料。英美對外關系研究室的具體工作主要是翻譯外文資料,在研究室的内部刊物《英美對外關系研究》上刊載,計劃在資料逐漸充實的基礎上再撰寫論文、出書。1965 年,從國外訂購的書陸續寄來,需要增加人手翻譯,這就從外文系調了幾個人,其中有張竹明。在王覺非先生的回憶錄《逝者如斯》中記載,在調來的人中“另有一人除俄語外,還懂拉丁語和古希臘語”。據張竹明回憶,他這次調動也有自身原因:一是他在外文系不熱心政治的态度引起一些人的不滿,總想批他,卻又批不成,這似乎成了一個麻煩,而調走麻煩就自然消除了。二是他在外文系裡開會時喜歡談論國際形勢,這樣做既可表示他關心政治,又比較安全,給人留下他對國際問題有興趣的印象,于是成了調往研究室的合适人選。他在研究室主要從事俄文資料翻譯,白天坐班,晚上繼續鑽研他的西文古學。有時不經意間古學也有特殊的功用。有一次,有人在翻譯時發現一句不明其意的文字,他認出這是用拉丁字母拼的希伯來文,弄懂了其意。這一時期他翻譯的大量俄文資料都沒能正式出版,倒是與人合譯的英文著作得以出版問世。張竹明年青時學的俄文後來發揮過一次作用,80年代初由他參與翻譯的《古代世界城邦問題譯文集》于 1985 年在時事出版社出版,後經劉小楓安排此書改名為《古代世界的城邦》又于 2011 年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
不久“文革”爆發,研究室的工作處于停頓狀态。這反倒成了他有較多時間讀書的特殊時期。比如,學校的掌權人通知每人帶小闆凳去操場開會, 他是人在會場,心馳天外,仔細聽的隻是會議開頭和結尾的發言,好供回去後談心得用,其餘時間則在背古希臘文。低調的态度保證他逃脫了被整的厄運,不整人又讓他不必勞神去誘人入罪。
“文革”結束後,一切逐漸步上正軌。他的工作小單位也有了變化,從英美對外關系研究室調入世界史教研室(一度分出世界古代中世紀教研室)。調動的原因一是個人興趣,他對古典學的愛好與國際關系研究畢竟遠些;二是外界的影響,70 年代末他去長春參加全國世界古代史學會成立大會,林志純(日知)先生鼓勵他歸位到世界古代史專業,同時他又參與了對“史學名著選讀”中李維《羅馬史》的譯文校訂。這就順理成章在系内做了一次小調動。
從研究人員轉為教師,工作的重心有了變化,教師以授課為主。除教通常的曆史主幹課外,張竹明開設較多的課程是古希臘文和拉丁文。教拉丁文是從1980 年開始,為bevictor伟德官网本科生開班,一連開了5次,古希臘文對研究生開了4次。學生有幾十人,而向專業發展最成功的隻有劉津渝一人。她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先是留校,後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古典學博士,現在在美國的大學教拉丁文、古希臘文和羅馬史,最近又被上海師範大學作為人才引進。劉津渝回憶:“到了大三,張竹明老師開拉丁語課,他是很懂行的,我古典語言這一攤就開蒙了。”其間他又被邀去東北師大古典所為本科生、研究生開設古典語言課。與他一起任教有一位天主教神父韓先生。他發現,他的拉丁文發音與韓先生有差異,似乎有學院派和教會派的區别,韓說張先生的發音是恺撒時代的發音,是古音。在東北師大教學結束時,他與學生合譯了一本拉丁史學名著《羅馬十二帝王傳》,1995年于商務印書館出版,算是對這段客居生活的紀念。他播下的古典語言種子,後又陸續長出幾株翻譯的枝丫。他與在bevictor伟德官网教過的學生先後合譯了幾本古典名著,計有與蔣平合譯的赫西俄德的《工作與時日 · 神譜》(商務印書館,1991年);與龍莉合譯的西塞羅的《論義務》(譯林出版社,201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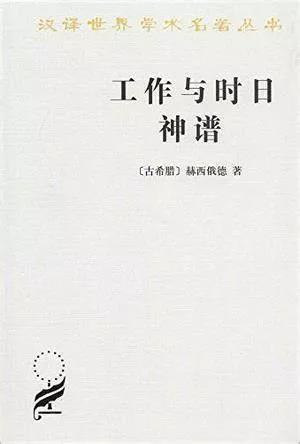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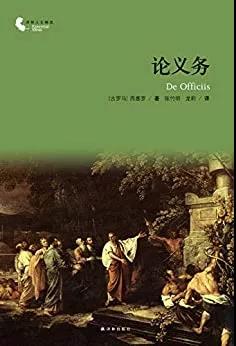
《工作與時日·神譜》與《論義務》
80年代前期,張竹明做的一件重要的工作是與郭斌龢先生合作翻譯柏拉圖的《理想國》。當時郭先生年事已高,難以獨立完成這一工作,商務印書館同意兩人合作。據張竹明回憶,他譯完全書後,送上譯稿,郭先生說:“全是你的辛苦。”郭先生提議自己署名第二譯者,并舉錢學森與助手合寫的書自己署名第二作者為例。張先生未加考慮,他認為錢學森是錢學森,這裡 這樣做是不合中國文人傳統道德的。該書的“譯者引言”是郭先生寫的,他也讓張先生修改定稿,張把引言壓縮了三分之一,包括一些容易引起政治誤解的東西,留下精華。張請老先生連同引言将譯稿通讀一遍,先生說“不用 了,我一讀書血壓就高”,并開玩笑說“你做事我放心”。“引言”對柏拉圖學術上的貢獻做了高度評價:“柏拉圖承先啟後,學究天人,根深葉茂,山高 水長,其人其學,成欤敗欤?我們有研究的必要。”其中又提到對柏拉圖其書的讀法:“柏拉圖《理想國》對話,為西方知識界必讀之書。見仁見智,存乎其人。毀之譽之,各求所安。關鍵在于細讀,慎思明辨之後,确有心得, 百家争鳴可也。否則斷章取義,遊談無根,那就了無意思。”這種文字還能見出昔日“學衡派”融彙中西的不凡功力。
張竹明在翻譯實踐中感覺,柏拉圖與亞裡士多德的文字全然不同,其揶揄的文風很難譯。他嘗試用文學筆調去譯哲學著作,對文字中的深沉意蘊做了細心的處理。張竹明自認這是他翻譯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從古希臘文直接譯來,也參考了其他文字(主要是英文)的譯本。他認為有些英譯本已很成熟,文字把握準确,是可以也應該參考的。古希臘文與中文的結構差别較大,借助其他文字譯本理解常有靈犀交會、忽有會心的感覺。2009 年,張竹明在譯林出版社又出版了經較多修訂的《理想國》新譯本,并以“柏拉圖論正義”為題寫了長達萬言的研究性導言。在這篇導言中,他談了自己對《理想國》的理解:“據我的理解,《理想國》主要讨論正義問題。包括究竟什麼是正義?怎麼才能實現正義?古希臘哲學到蘇格拉底發生了曆史性的轉折。‘認識你自己’的口号把哲學從對自然的研究拉向了對人生的研究。蘇格拉底看到人類本質上是思想的動物,他認為人類應當不斷地追求智慧、追求真理,并倡導一種獲得知識的方法,即提出定義并通過讨論或辯駁對之進行檢驗。以人為中心,對各種人生問題讨論‘×× 是什麼’,就是通過尋找事物的定義弄清楚事物的本質。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是通過蘇格拉底(作為柏 拉圖的代言人)和談話助手們的反複诘難來尋求正義定義的推理過程。”
張竹明在西方的古典作品中比較偏愛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著作,總是感到它們似乎永恒地界定了一種高度古典的風格。英國哲學家伯納德 · 威廉 斯說:“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界定了一種古典的哲學風格—宏大、威嚴、全面的哲學風格。這兩位哲學家過去始終引人入勝的原因不僅在于他們無可置疑的敏銳性、洞察力和想象力,人們還相信,他們擁有宏大整合的體系抱負。”正是基于這一考慮,他用了很大精力去譯介這兩位古典大師的著作。
1992 年退休後,張竹明承接了一項巨大的翻譯任務。有一天,江蘇譯林出版社的編輯登門拜訪,說是慕名而來,想請張先生承擔翻譯全部古希臘戲劇作品的重任。據說這是國家新聞出版署的一個重點項目,有好幾個出版社競争,但當譯林出版社提出聘請的譯者将從古希臘原文翻譯時,這一項目就自然被譯林出版社競得。承擔這樣大部頭的外國古典作品翻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将古希臘羅馬原典介紹到國内又是他畢生的志向,于是就答應了出版社的約稿,約定以五年為期交稿。出版社對譯稿有兩點要求:一是要從古希臘原文翻譯;二是署名隻署張竹明一人。因為部頭太大,張竹明提出可否與人合作,讓人從英文先譯出,他再據古希臘文校對,出版社不同意,堅持原來的要求。在譯文形式上,出版社主張采用詩體。因為古希臘文的詩歌沒有尾韻,張竹明希望用散文體翻譯,出版社也不同意。如何用詩體翻譯古希臘作品,對此他早有過考慮,曾經設想過用楚辭的離騷體翻譯荷馬史詩,因為楚辭的格式比唐詩自由,可以用長短句。對如何處理古希臘戲劇作品的譯文分行問題,他考慮了很久,希望譯出的文句有詩的韻味,便于朗誦。最後想了個簡便的辦法:将句子譯出詩的抑揚頓挫,平均每行譯成兩個半起伏,長度與原詩大緻相仿。
答應容易,真正做起來才發現難處不少。估計全部的譯文字數在 300 萬字以上,後來印出來有八卷之多,工作量很大。速度上不去的另一個原因是他不會用電腦,全靠手寫筆錄。每天是繁複的案頭譯事,日出而作,日落不息,足不出戶,日複一日,在行行對話、詩句中斟酌傳言。未想到這一工作不像他當初想得那樣順利,五年時間過去,進度才完成三分之一,需請人加盟。他先邀請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長廖學盛(曾在蘇聯學習古典史學)合作,廖先生沒有時間,介紹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王煥生研究員(也是在蘇聯學古典語言的海歸),由王先生承擔新喜劇及埃斯庫羅斯作品的翻譯,約占四分之一,後印成兩卷。以前羅念生、周作人和楊憲益曾譯過其中部分作品,對這些譯作可以參考,但在具體表述上不同譯者有不同的理解。對參考前人譯本,張竹明稱之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對前輩的拓荒之功不應忽視。在參考前人譯作時張竹明也有“發現”,如周作人的譯作《财神》譯得最好,楊憲益譯過《鳥》,文字極為典雅,但其後半部譯得過于自由。出版社也很有耐心,譯稿完成一個劇本就編定一個,然後再耐心地等,就這樣等了十年,全書才最終譯完,真可謂十年磨一劍。《古希臘悲劇喜劇全集》于2007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裡庇德斯的悲劇以及阿裡斯托芬和米南德的喜劇,涵蓋了古希臘所有存世悲劇作品 32 部和所有存世喜劇、新喜劇作品 18 部,最為齊全周詳。該書出版後轟動一時,影響很大,在北京召開了專家座談會,遊本昌、史可等著名演員做了化妝表演,朗誦了新譯劇本的片段。該書還獲得“第二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圖書獎”等榮譽,一時間好評如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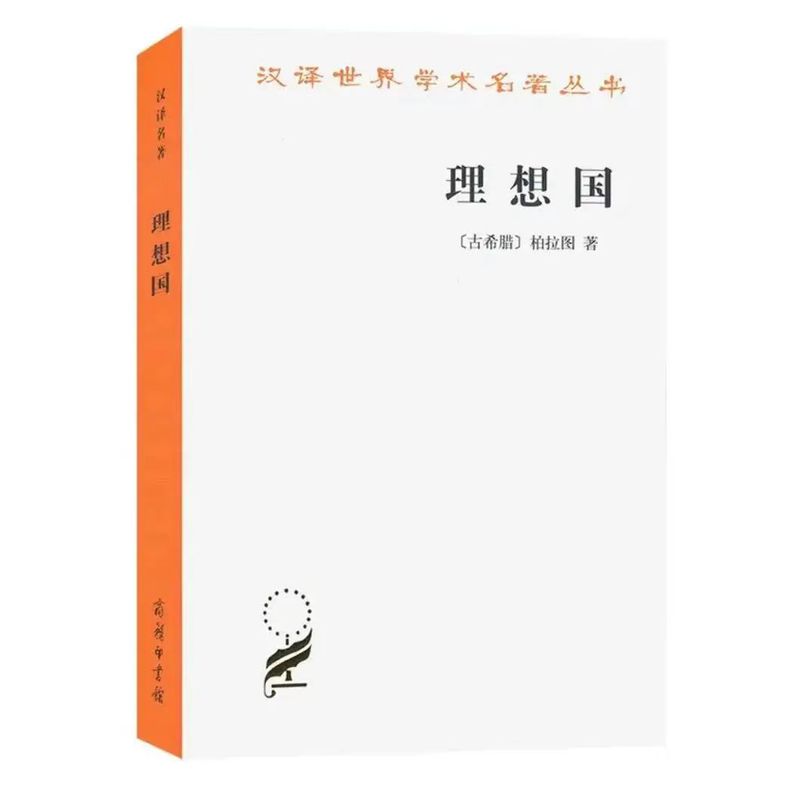

《理想國》與《古希臘悲劇喜劇全集》
2012年底,80 高齡的張竹明在女兒陪同下應邀去中山大學,給該校博雅學院的本科生開講座。按規定,博雅學院的學生要“在四年本科期間廣泛深入研修中西方文明傳統及其經典著作,必修古漢語、古希臘語、拉丁語等古典文明語言,兼修藝術理論及其技能”。在講座之後,博雅學院那些稚氣未脫的年青人圍着他,手裡拿着他譯的書請他簽名。面對這麼多朝氣蓬勃、熱情專注,有志研習古典和傳統的年青學子,看到自己一生從事的冷門古學居 然有這麼多的後繼者,聯想到自己當初苦心孤詣的寂寞境界,竟情不自抑,老淚縱橫地說:“真是相見恨晚,相叙恨短啊!”他感慨:西方古典學在中國傳承及發揚,并能為我所用,需要一定數量的有心人學習古希臘文、拉丁文,研讀古典文獻,對文學、曆史、哲學有相當的了解,并有獻身精神,這樣才能有所成就。這些稚氣未脫的學生或許就是未來的希望。接着,他又去廣東肇慶,參加了中國古典學和西方古典學的比較學首屆年會,看到與會者有一百多人,也有同樣的心情。
 張竹明先生與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同學座談,2012年12月
張竹明先生與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同學座談,2012年12月

張竹明先生與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同學座談,2012年12月

張竹明先生與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同學合影,2012年12月
他對西方古典學在中國的發展有一個整體的考慮:希望一步一步地推進,先讀通原著,譯成漢語,逐漸積成規模,再考察原作者的思想及其時代,然後才是縱向和橫向的探究,進行中西比較,互相吸收,各取精華。他覺得,現在國内對西方古典學的研究尚處于佛學發展的玄奘階段,需要有大量準确、優質的翻譯。他認為自己的翻譯不能說有多麼優質,但還是比較可靠的。
2013年5月16日,應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學生會邀請,張竹明給校内的本科生、研究生做了一場題為“我的治學之路”的講座。在講座中,他坦言:“有人跟我說,學希臘文和拉丁文很苦,要長期堅持,花很多功夫,當你把希臘文掌握得很熟了,别人花同樣時間能寫出多部專著,你劃不來。你怎麼會想到走這條路的呢?我的答複是兩個字:‘熱愛!’我嘗到了它的甜頭,我愛上古希臘文、拉丁文所承載的文化,因而也愛上了這兩種文字,所以不怕苦。”對初入學術殿堂的莘莘學子,他根據自己對西方古典的多年感悟,向他們指出探求的門徑:“研究西方古典學應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為重點。蘇格拉底以前,古希臘的哲學研究人生活的外部世界,追尋大自然的本原。但是這一工作好像一個天生的盲人和一個後天緻盲的人讨論太陽的顔色是紅還是黑的一樣,無法達成共識。蘇格拉底認為,問題出在認識的主體上,是人在認識外部世界,所以先要研究人本身。他提出口号‘認識你自己’,也就是要研究認識的主體。他提出的第二句話是:‘美德就是知識。’人生來就有追求确實可靠的、永恒的真知識的傾向。那麼這個真知識是什麼呢?蘇格拉底沒有明說,但結論很清楚,就是存在于思維中的‘概念’。接着,柏拉圖提出‘善的理念’點明了這一點。亞裡士多德提出脫離物質的 ‘形式’。它們都是蘇格拉底這一思想的繼承、發揚、提高。蘇格拉底一生無一字著述,後人說他抵得上半個歐洲的圖書館,就是因為他創造了人生哲學,使人類的認識活動發生了一次劃時代的轉向,接着便出現了知識的大爆炸。亞裡士多德全面創建了幾乎遍及自然、人文、社會、藝術、思維的各門學科。”他多麼希望此時聽講的年青人都能成為熱愛先哲、熱愛古學,熱愛知識的讀書種子呀!
本文刊于《世界曆史評論》05 古典學在中國,作者陳仲丹,bevictor伟德官网曆史系教授。

前排坐者右起:張竹明老師、張樹棟老師;後排站立者:右二為文章作者陳仲丹教授

